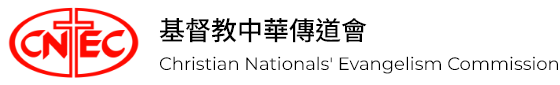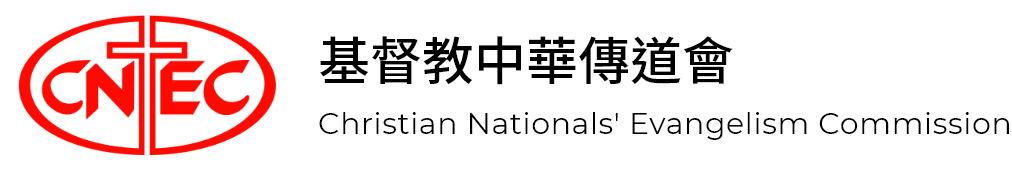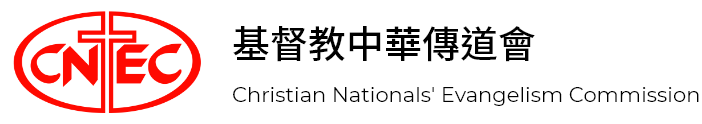信息文章
堂會招聘信息
盛福堂 全職傳道 職責:負責牧養駐校堂會,協調堂校⼯作 要求:需神學畢業,具教導、團隊精神、主動溝通,並關顧及栽培青少年,支援差傳及關懷探訪 請將履歷電郵至中華傳道會盛福堂hr@shingfuk.org 恩光堂 全職傳道 職責:策劃及帶領兒童及青少年團契,願意牧養兒童、青少及婦女,並看重講壇宣講 要求:需神學畢業,主動積極、盡責及重團隊合作精神 堂會位於大埔富善邨,有意應徵者請繕履歷至 cnecglc@gmail.com,合則約見面洽
不是偉⼤事的社區服侍
原文刊載於《時代論壇》第1701期(2020年4月5日) ⼀間位處於⼤廈的教會要做社區服侍⼯作,其實是有難度的,街坊對我們的印象多是與信仰有關。當我們主動接觸他們時,他們先是會怕「被踢入會」,⼜因為不知道教會裡的情況如何,就對我們有所保留。不過,若然透過與社福機構合作,針對這些基層的缺乏:先是物質上再到⼼靈上,服侍就會比較到位。 感恩神帶領著我們。事⼯初期,我們合作的機構有兩類:⼀是做食物銀⾏的。街坊會到食物銀⾏,⾃然是有物質上的需要,機構明⽩這些家庭在物質以外,⼼靈上也是有需要的。所以他們希望與同區教會合作,期望教會以信仰⾓度去關顧家庭。另⼀類合作機構是非常積極做前線探訪的,他們的經驗與同⾏成了我們的祝福,⿎勵了久被困於四道牆內的教會,走出去社區做服侍。 回顧這些年的服侍,我們發現教會在社區服侍這事上,既是被動也是主動的。我們最初主動想透過功課輔導班做福⾳⼯作,教會⾨開了,鄰舍卻不積極入來。意外的是:⼀個平⽇,在⼤廈管理處閒坐的婆婆,她並非我們的會友,但竟⼤⼒幫我們宣傳,叫了好幾個家長把⼩朋友送來教會。更有意思的是,這個婆婆後來也開始到教會來。她告訴我們,她年輕時去過教會,受過恩惠,⽣命經歷了好多事;雖然⼀直未決志,也沒有好好「入教」,但⼼裡⼀直是「信主」。 婆婆最後在我們教會決志信主,上天家之前,還拜託教會負責她的安息禮拜。她說⾃⼰最終都回到天⽗家裡,最後的⽇⼦⼼中很平安。 另⼀個幫助我們走進社區的⼩天使,其實也不是「教會⼈」,她是我們功輔班的家長。她因為沒有錢可以給女兒補習,⾒到教會有免費的,她就來了。她是⼀個無神論者,對她⽽⾔,教會的⼈都是善⼼的,她樂於跟我們做朋友,但信仰免談。因著欣賞我們的善⼼,所以當我們說想接觸更多社區有需要的家庭時,她積極與我們分享⾃⼰的經驗和⼈脈,給我們很⼤的幫助。她的孩⼦很乖,來了功輔班後,學校成績⼀直進步,⼈也是開朗了。 孩⼦對福⾳開放,聽說媽媽曾經把她帶去佛堂不知道學甚麼,但孩⼦去了不舒服,堅決不再去,還勸媽媽要來教會。⼩學畢業後,她考入了⼀間不錯的中學,媽媽⼀直跟⼈說是教會把孩⼦教好的,這孩⼦在中⼀時決志信了耶穌。因為有在教會學琴,現時在兒童團契有司琴的服侍。 我們每年都有福⾳晚餐,或不時有社區福⾳佈道,這個媽媽在兩年前⼀次聚會中也決志了。她說⾃⼰本來很⼼硬,誰也不信,只信⾃⼰⼀雙⼿,但帶著女兒在香港⽣活,遇上很多說不出的難處,讓她不得不放下⾃⼰。⽽在這些困難的⽇⼦裡,教會(她接觸不少⼟瓜灣的教會)給她關⼼和幫助,使她感受到愛。她說現在願意信耶穌,⼜把女兒交託教會,願意讓耶穌帶領她。 這些⽣命故事,激勵了我們服侍社區的⼼。弟兄姊妹由開始時不會刻意接觸街坊,從來不知道那些舊樓的⽣命故事;到現在,我們對街坊愈來愈開放,對社區的需要和關⼼都是積極的,⼤家會樂意去探訪。如果知道有服侍的機會,總是願意付出,不論⾏動上或⾦錢上,甚⾄弟兄姊妹會動員⾝邊⼈來參與,成為很美的⾒證。 有⼈以為教會做社關就是為滅貧,⽽滅貧應該是政府的事,這種不可能任務,教會既做不來也不⽤做,我們只需要專⼼傳福⾳就可以了。但正如德蘭修女說:「不是我們可以做偉⼤的事,但我們可以⽤偉⼤的愛做⼩的事情。」教會也應該可以如此服侍。
城寨中的恩光
本文取自香港神學院網站「港師分享」 近日,得獎電影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再次上映。一年前,當這套電影推出後,城寨這個充滿傳奇色彩的地方再度成為焦點,許多基督徒也重新關注到宣教士潘靈卓(Jackie Pullinger)昔日在城寨的工作,其著作《追龍》在基督教書室更成為了暢銷書。她以服侍「窮人中最窮苦的人」(the poorest of the poor)為使命,在城寨中幫助吸毒者、黑幫少年、妓女和露宿者,將基督的愛帶給他們,其無私付出使她獲得「港版德蘭修女」的稱譽。 除了潘靈卓的工作,城寨歷史上也曾出現其他基督教事工。今天九龍寨城公園裡有四塊太湖石,紀念五位曾對城寨居民作出貢獻的傳道人:鄺日修、劉知三、潘靈卓,以及韋麟趾(Rick Willans)和韋真示東(Jean Stone Willans)夫婦。其中最早開展事工的是香港聖公會牧師鄺日修,他在1900年代於城寨開辦「廣蔭院」(正門門旁牆上寫著「耶穌教窮人院」1)、學校和藥局,為貧苦大眾服務。今天公園內的舊衙門,門楣上刻有“ALMSHOUSE”字樣,標誌著當年窮人院的所在地。 另一位華人傳道者劉知三是中華傳道會的牧師,他在1950年從內地移居香港,在孤苦的生活中認識了基督信仰,並在信主後不久已接受神學裝備,期間也開始進入城寨工作。2 1950年代初,隨著大陸變色,大量內地人湧入香港,城寨人口迅速增加。中華傳道會開始關注到這裡的需要,並在1952年開展佈道工作,最初以流動露天佈道形式進行。後來,一位老姊妹借出家中小廳,讓中華傳道會得以開辦「西頭村佈道所」。當時香港聖經學院(香港神學院前身)剛成立不久,佈道所的福音工作由學院和九龍城福音堂(活水堂前身3)共同承擔。4 那時城寨內的海洛英(白粉)貿易日益猖獗,吸毒者眾。雖然當時仍有人吸食鴉片,但由於白粉價格相對低廉,而且吸食工具簡單,許多窮困潦倒的人轉而吸食白粉,並因吸食過量而昏厥。佈道同工每次進入城寨,總在暗黑的街巷中看到死屍橫陳,尤其是公廁附近。5 1956年,中華傳道會在城寨龍城路開辦「慈光贈診所」,不僅為貧病者贈醫施藥,也為吸毒者提供戒毒治療。診所上層還為吸毒者子女開班,讓孩子有一個棲身的避風港,並在其中認識基督的愛和盼望。6 1960年,中華傳道會在龍津道一棟四層高唐樓成立「中華傳道會福音中心」,上述佈道所和診所合併於福音中心,並分別更名為「恩光福音堂」和「恩光贈診所」。7福音堂每週均有佈道、崇拜和主日學等聚會,並設有慕道查經班。除了佈道所和診所,1953年在九龍城南角道開辦的「九龍城福音堂平民義學」亦遷入福音中心,8並易名「德成分校」,最後改名為「恩光學校」。學校提供幼稚園至小六教育,學生多數來自城寨。9 後來,福音堂併入附近的活水堂,診所則遷至油塘灣,因為診所的醫生對吸毒者經常故態復萌感到失望。此後,福音中心便主要由學校使用。10在龍蛇混雜、罪惡淵藪的城寨,良好的品德教育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,使孩童不致誤入歧途。而校內的福音工作,也使恩光照亮這片土地,拯救了不少迷失的小靈魂。 1847年建成的九龍寨城衙門(九龍巡檢司衙署),是唯一獲保留在今天九龍寨城公園內的古建築,它不僅是昔日清政府主權的印記,也遺下城寨基督教事工的痕跡。鄺日修牧師在1902年創辦的廣蔭院,1918年由香港基督教聯會接辦,並易名「廣蔭老人院」。後來更寬敞的鑽石山廣蔭老人院落成啟用,城寨的老人院在1969年停止運作,院友悉數遷往鑽石山。111971年,中華傳道會租下衙門供恩光學校使用,並將該處命名為「恩光園」。高峰時期,學校有超過420名學生。學校強調教育與福音並重,引領了許多學生信主。12 然而,到了1970年代中期,學生人數開始減少。由於城寨的學校不獲政府承認,學生無法參加公開試升讀中學,加上港督麥理浩於1978年實施九年免費教育,許多學生轉往外校讀書。恩光學校最終於該年停辦,只剩幼稚園繼續運作。13 早年除了劉知三牧師,中華傳道會還有張祖鷺牧師參與城寨的服侍,兩位牧師一家都在城寨居住。當年兩位牧師得知城寨住了六百多位長者,由於城寨樓宇非常密集,長者家中有窗也不能打開,室內長期不見天日,而恩光園是城寨唯一沒建高樓的地方,兩位牧師便決定將學校改為老人中心,為長者提供理想的休憩場所。老人中心於1979年正式開辦,一直營運至城寨清拆前,期間共有三十位長者受洗。最高峰時,中心共服務187名會員。14 1991年,老人中心遷至大埔富善邨現址,並改名為「中華傳道會恩光老人中心」,此外也在同址建立「中華傳道會恩光堂」,1992年4月舉行首次主日崇拜。15老人中心後來提昇為「中華傳道會恩光長者鄰舍中心」,服侍區內長者和護老者。16雖然城寨經已清拆,但恩光園的事工在上帝的恩典下得以延續,繼續服務社區。 雖然城寨是黃賭毒的溫床,罪犯輻輳之地,但其實一般居民都能夠相安無事地生活,中華傳道會的事工也從未受到干擾。劉知三牧師憶述:「我自1971年就在城寨居住,什麼也不怕。從五十年代中期起,我就經常出入;到了六十年代,城寨街巷有很多道友,從學校天台往下望,總見到他們蹲在道中。還有賭檔、色情場所和真人表演。但這些都在七十年代中,慢慢銷聲匿跡。沒有人來找過我麻煩,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們是為城寨居民謀福利。」17 過去,上帝的事工在這片三不管地帶發揮了重要作用,為有需要者帶來了恩光。回顧這段歷史,我們不僅看到城寨陰暗和混亂的一面,還看到傳道同工如何以愛心實踐全人關懷,為無數落魄之人帶來希望。前人不畏艱難服務窮困者的精神,實為今天信徒的楷模。 註釋:1. 吳邦謀:《從啟德赤鱲角》(香港:中華書局,2022),頁40圖片。2. 格雷格‧吉拉德、林保賢:《黑暗之城:九龍城寨的日與夜》(香港:中華書局,2015),頁310。3. 最初為1951年在西頭村竹娘街一石屋創辦的「西頭村福音堂」,翌年遷至九龍城南角道,易名「九龍城福音堂」,1964年再改名為「活水堂」;〈活水堂史略〉,《中華傳道會銀禧紀念特刊》(香港:中華傳道會,1968),頁8。4. 金振宇:〈中華傳道會恩光福音中心〉,《中華傳道會銀禧紀念特刊》(香港:中華傳道會,1968),頁248。5. “Drug Victims Rescued from Living Hell,” Crusade (July-August 1958), p. 3.6. “Further Work,” Crusade (July-August 1958), p. 10.7. 金振宇:〈中華傳道會恩光福音中心〉,頁24。8. 〈福音中心〉,《傳道通訊》創刊號(1960年7月),頁45。9. 金振宇:〈中華傳道會恩光福音中心〉,頁24。開幕時,學校已招收了260名學童;〈福音中心〉,頁45。10. 金振宇:〈中華傳道會恩光福音中心〉,頁24;及格雷格‧吉拉德、林保賢:《黑暗之城》,頁310 11. 邢福增、劉紹麟:《天國.龍城: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(1890-2009)》(香港: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,2010),頁62-66;及〈鑽石山廣蔭老人院 舊址正式交還政府〉,《時代論壇》第 2960期(2021年5月23日),〈https://christianweekly.net/2021/ta2040465.htm〉(2025年2月13日下載)。12. 劉知三:〈恩光老人中心〉,《中華傳道會五十週年金禧特刊》(香港:中華傳道會,1993),頁50。13. 劉知三:〈恩光老人中心〉,頁50;及格雷格‧吉拉德、林保賢:《黑暗之城:九龍城寨的日與夜》(香港:中華書局,2015),頁313。14. 劉知三:〈恩光老人中心〉,頁50-51。15. 劉知三:〈恩光堂〉,《中華傳道會五十週年金禧特刊》(香港:中華傳道會,1993),頁32。16. 〈中心簡史〉,〈https://cnecglnec.org/main-page/關於我們/中心簡史/〉(2024年10月30日下載)。17. 格雷格‧吉拉德、林保賢:《黑暗之城:九龍城寨的日與夜》,頁314。
港神打卡點:Jepson Hall
本文選自香港神學院院訊(第171期,2023年9-10月) 香港神學院校舍舊翼有一座翟普生堂(Jepson Hall),自1960年代以來一直是本院的標誌性建築。1960年,由中華傳會創辦的香港聖經學院(本院前身)從界限街156號的校舍,遷移至新租賃的金巴倫道17號,並於1966年正式購得該址。1968年4月27日,學院舉辦了「中華傳道會港台澳教區銀禧紀念暨翟普生堂奉獻典禮」,1翟普生的遺孀Mrs. Margaret Jepson 出席了是次活動。2翟普生究竟是誰?為何本院的主樓會以他命名? 翟普生 (Nis Alvin Jepson,1888-1951)本身是美國一位脊骨神經科醫生,3同時也是西雅圖基督徒商人團契(Christian Business Men's Committee of Seattle) 的主席。4基督徒商人團契於1930年建立,其時美國正值經濟大蕭條,多地興起了關注拯救靈魂的熱心信徒。各地的中堅分子於1937年在芝加哥聯手成立了「國際基督徒商人團契」(International Christian Business Men's Committee),其中翟普生擔任了副秘書(Vice-Secretary)。5他一直致力向平信徒傳遞普世宣教的使命,並主張讓各地的基督徒向自己的同胞傳福音,但卻缺乏將這願景付諸實行的途徑。6 及至1942年,前內地會宣教士麥克德肯(Duncan McRoberts,1912-2000)由中國返回美國,這為翟普生提供了實踐理念的契機。麥克德肯自1936年起在江西景德鎮傳教,他的宣教經歷使他認識到,華人自傳比西教士的傳道更有果效,中國教會的未來也必須掌握在中國人手中。此外,麥克德肯開始在華傳教不久,中國便進入八年抗戰階段,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,中國加入同盟國陣營,突變的局勢對在華傳教工作造成重大影響。許多傳教士不得不返回本國,而教會的領導工作,便需要交由中國基督徒來承擔,這使麥克德肯看到培育華人自傳的需要更為殷切。翟普生與麥克德肯的想法相當配合,於是二人便開始合作推動異象。7 翟普生安排了一些基督徒商人與麥克德肯會面,這群商人早前在翟普生的帶領下,成立了一個為中國失喪靈魂禱告的小組。據說麥克德肯分享的內容包括:「戰爭期間不需要送西教士去中國了,西教士每回去中國,要先用六年學話,七年回國一次,然後再回去傳道,等於十年才能產生一個人,現在為甚麼不用少數的錢去接濟一個中國傳道人,要他們作開荒傳福音的工作⋯⋯特別是打仗期間交通不方便。」8 這群商人十分認同要由美國基督徒提供經費,支持中國基督徒自傳和訓練本地傳道同工,建立本色教會。他們最終於1943年4月在西雅圖創建了宣教組織「中國基督徒佈道十字軍」(China Native Evangelistic Crusade,簡稱“CNEC”,「中華傳道會」前身)。翟普生出任了首屆會長(直至1951年),當時在貴州傳道的趙君影被委任為監督。總部最初設於貴陽,翌年遷至陪都重慶。9中華傳道會的在華工作,便在這戰火時期正式展開。 從歷史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,除了佈道工作,神學培訓早已是佈道十字軍的重點工作。1952年香港聖經學院的成立,充分體現了先賢對培訓本地工人的重視。而“JepsonHall”這名字也提醒著我們,曾經有一群愛主的信徒,在烽火連天、動盪時勢中,仍關注到各地人民的心靈和福音需要。在今天劇變中的香港,前人的見證與經驗成為了我們重要的明燈,引導我們在任何處境下都不忘主的使命。 1. <盡心:1952-1951>,《香港神學院五十週年金禧紀念特刊》(香港:香港神學院,2002),頁31;及<盡力:1962-1971>,《香港神學院五十週年金禧紀念特刊》(香港:香港神學院,2002),頁32。 2. "People in the News," The King's Business 58:12 (December 1968), p. 7. 3. "The History of WorldShare.” <https://worldshare.org.uk/download-file/downloads/orldShare_FulL History.pdfs (accessed 12 July 2023). 4. Paul W. Rood, “Around the King's Table,” The King's Business 29:3 (March 1938). p. 91. 5. Rood, “Around the King's Table,” p. 91; and “CBMC History,” <https://neohio.cbmc.com/about-neohio/history-of-cbmc> (accessed 12 July 2023) 6. “The History of WorldShare,” ehttps://worldshare.org.uk/download-filerdownloads/oridShare_FulL_History.paif> (accessed 12 July 2023) 7. “The History of WorldShare”;及郭偉聯:《抗戰時期的學生佈道運動:兼論社會及教會轉變》,李金強、劉義章編:《烈火中的洗禮:抗日報爭時期的中國教會1937-1945》(香港:建道神學院,2011),頁 391。 8. 于力工:《夜盡天明:于力工看中國福音震撼》(台北:華人文宣基金會總經銷,1998),頁169。 9. 參與成立佈道十字軍的美國基督徒商人包括 Cephas Ramquist、Krist Gudnason、Cecil Kettle、Einer Anderson 及 Charlie Cooper。 "The History of WorldShare”;郭偉聯:<抗戰時期的學生佈運動:兼論社會及教會轉變>,頁 392;鄭德富:〈中華傳道會的創立和發展簡略)(2003年7月),<https:/hwww.lws.edu.hkizh_tw/siteNview?name= 中華傳道會的創立和發展間略>(2023年7月12日下載);及“Brief History of CNEC”, <https://www.lws.edu.hk/tc/school-history>(2023年7月12日下載)。